李怀安:旧书余韵
李怀安:2025-10-13 来源:原创
评论:(0) 阅读:(85)
在电子屏幕统治视觉的年代,我仍固执地眷恋着旧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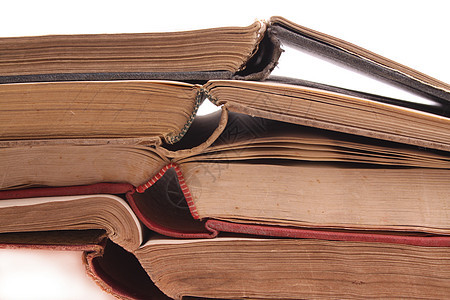
在电子屏幕统治视觉的年代,我仍固执地眷恋着旧书。并非迷恋其中的知识——那些大多已数字化,而是贪恋一种唯有旧书才能给予的、综合的感官体验。那是一种由视觉、触觉与嗅觉共同编织的,关于时光的诗意。
我的书架深处,有几册民国年间的旧版书。它们的封面是朴素的,甚至有些残破,纸张也已泛黄发脆,呈现出一种被称为“沧桑”的独特色泽。那不是衰败的颜色,而像是时光浸染的琥珀,将一段过去的岁月完好地封存其中。指尖轻抚纸面,能感受到那种微糙的、带着纤维质感的纹理,与如今光滑的铜版纸截然不同。
最令人沉醉的,是它的气味。将书页凑近鼻尖,一种复杂而温和的香气便幽幽传来。那是干燥的纸浆、微弱的墨香,以及岁月本身混合的味道。有人说,这是“霉味”,可我更愿称之为“书卷气”。它不像香水那般张扬,而是内敛的、沉静的,仿佛一位饱学宿儒平静的呼吸。这气味,能瞬间将人拉离当下,置身于一个想象中宁静而悠远的时空。
翻阅这些旧书,常会与往昔的读者不期而遇。有时是页眉页脚寥寥的铅笔批注,字迹清秀或潦草;有时是划过某段文字的浅浅线痕,透露着当时阅读者的心潮起伏。在一本《陶庵梦忆》里,我曾见一枚压得平整的银杏书签,虽已枯黄,叶脉却依然清晰。我常想,是哪位前辈,在哪个秋天的午后,随手拾起这片叶子,夹进了他正神游的晚明旧梦里?这种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,让阅读不再是独自的探索,而成了一场与前人精神的共舞。
这些旧书,大多阅读起来并不“方便”。没有随点随查的链接,没有调整字体大小的自由。但这种“不便”,恰恰要求一种全神贯注的、缓慢的沉浸。在它们面前,你快不起来。你必须适应它的排版,它的句读,甚至它偶尔的缺页与污损。正是在这种缓慢的磨合中,你与书本建立了一种更为亲密、更为郑重的关系。阅读,因此而成为一种仪式。
它们静静地立在架上,于我,却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袖珍故乡。在纷繁扰攘的间隙,抽出一册,无需细读,只是摩挲着那温厚的书脊,嗅闻那熟悉的幽香,心便能很快沉静下来。它们提醒我,在这个追求“新”与“快”的时代,有些价值的沉淀,恰恰需要“旧”与“慢”。那书页间残留的,不仅是油墨与纸张,更是一段段活过的生命,以及一份在时间长河中,始终未曾褪色的温情与敬意。

文章评论
最热评论
资讯更多 >

2016年“年末”征文获奖名单
- 一等奖(2名)王朔、资中筠
- 二等奖 (2名)应连新、向叶平
- 三等奖 (3名)张震 、朱永德、马路
2016年度,文易通宝年度获奖名单
- 文易通宝“突出贡献奖”:
- 刘文敏、杜绍营、韩静、张殿兵
- 文易通宝“文学新秀”称号:
- 高康康、 王梦媛、曾梦情、宋万友


 我要投稿 >
我要投稿 > 我要报名 >
我要报名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