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见晴:黑板下的粉笔灰
苏见晴:2025-12-25 来源:原创
评论:(0) 阅读:(60)
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摊开手掌。指腹上似乎还残留着那细腻如尘的触感。那不仅仅是粉笔灰,那是无数个“当下”在成为“过去”时,留下的、最轻也最重的遗骸。而我们,就在这不断的书写与擦拭、建立与抹去、铭记与遗忘的循环中,跌跌撞撞地,长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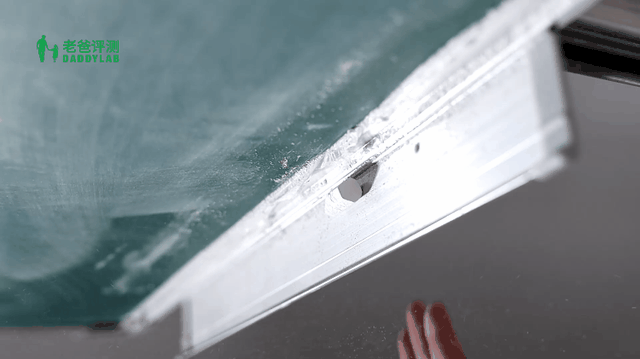
周五放学前的大扫除,我被分配去擦黑板。不是用湿抹布敷衍了事那种,是彻底的清理。需要先用板擦将前一天残留的白色字迹用力擦去,扬起一阵呛人的白雾,然后用湿抹布一遍遍擦拭,直到墨绿色的板面露出湿润的、深沉的本色,最后再用干抹布抛光,使其在灯光下泛出哑光。
我干得很卖力。板擦与黑板摩擦,发出“唰唰”的、干燥而有力的声响,白色的粉尘像微型雪崩,从板面上倾泻而下。粉笔灰并不完全听话,它们一部分被板擦吸附,更多的则扬到空中,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夕阳光柱里,形成一道缓慢扩散、翻滚的云雾,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沉降。
终于,黑板洁净如新,像一片深绿色的、宁静的湖泊。我颇有成就感地退后两步欣赏,却在这时,目光被黑板下方那道狭长的、金属制的粉笔槽吸引了。
槽里并非空空如也。
那里积着厚厚一层粉笔灰。不是刚才擦黑板时落下的新鲜灰烬,而是经年累月、层层叠叠、被无数次擦拭遗漏,最终沉淀下来的“陈年老灰”。颜色不是纯白,而是一种混合了灰尘的、黯淡的灰白色,像河床底部细密的淤泥。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,紧贴着槽底,蓬松,柔软,却又带着一种沉重的、被遗忘的质感。
我蹲下身,与粉笔槽平齐。
细看之下,这层灰并非均匀。有的地方厚些,堆成小小的、舒缓的丘陵;有的地方薄些,露出底下金属的冷光。边缘处,灰粉与槽壁的结合部,形成一道道极其细微的、波浪状的纹理,那是日复一日,板擦挥动带起的气流,像微型的风,在这里留下的雕刻痕迹。
我忽然意识到,我面对的,不是垃圾。
这是知识的骨灰。
是牛顿定律被反复推导后留下的粉末,是古诗词被深情朗诵后飘落的余烬,是化学方程式在空气中爆炸后的沉降物,是历史年表被一遍遍描摹后磨损的残骸。每一粒微尘,都可能来自某位老师用力写下重点时崩断的粉笔头,或者某次值日生匆忙擦拭时未能尽收的疏忽。
它们曾经是清晰的笔画,是确凿的公式,是试图被传递和理解的意义。然后,在完成了“表达”的使命后,它们被抹去,被否定,被归零,最终降解为这最原始、最卑微的形态,汇聚在这道不为人注意的凹槽里。这里是一个终点,所有黑板上的辉煌、努力、乃至错误,最终都归宿于此。
我伸出手指,极轻极轻地,碰了一下那灰层的表面。
触感比想象中细腻,像最上等的天鹅绒粉末,却又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枯寂。指尖留下一个清晰的小凹坑,周围的灰粉微微塌陷,但没有任何声音。这寂静比任何喧哗都更震耳欲聋。它们曾是声音(粉笔书写声),曾是视觉(白色字迹),现在,什么也不是了。
走廊里传来同学催促回家的笑闹声。我该清理掉它们了。这是大扫除的职责。
我用小刷子,小心地将这些粉笔灰扫进簸箕。它们很轻,扬起一小团迷蒙的雾,在夕阳的光里最后闪动了一下,便乖乖地被收纳。倒入垃圾桶时,它们与其他杂物混合,彻底失去了独特性。
我洗净了手,背上书包。离开教室前,最后看了一眼光洁的黑板,和空空如也的粉笔槽。
明天,新的字迹又会被写上,新的公式将被推导,新的知识将以白色的、醒目的形态,占据那片墨绿。而粉笔槽,将继续它沉默的、收纳一切“过往”与“废弃”的工作。
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摊开手掌。指腹上似乎还残留着那细腻如尘的触感。那不仅仅是粉笔灰,那是无数个“当下”在成为“过去”时,留下的、最轻也最重的遗骸。而我们,就在这不断的书写与擦拭、建立与抹去、铭记与遗忘的循环中,跌跌撞撞地,长大。
上一篇:莫语:倾听暖气管
下一篇:谢停云:课桌里的旧试卷

文章评论
最热评论
资讯更多 >

2016年“年末”征文获奖名单
- 一等奖(2名)王朔、资中筠
- 二等奖 (2名)应连新、向叶平
- 三等奖 (3名)张震 、朱永德、马路
2016年度,文易通宝年度获奖名单
- 文易通宝“突出贡献奖”:
- 刘文敏、杜绍营、韩静、张殿兵
- 文易通宝“文学新秀”称号:
- 高康康、 王梦媛、曾梦情、宋万友


 我要投稿 >
我要投稿 > 我要报名 >
我要报名 >